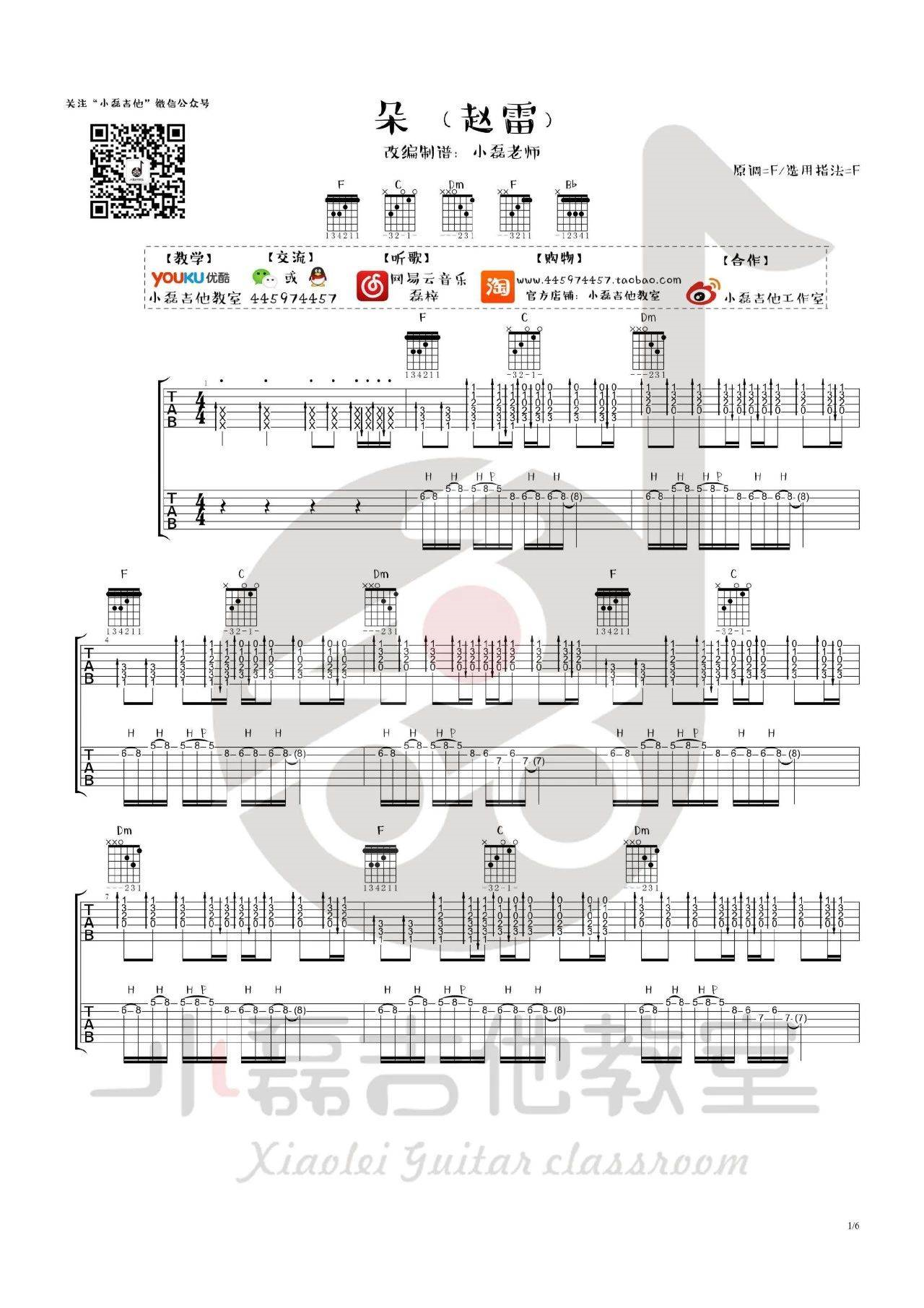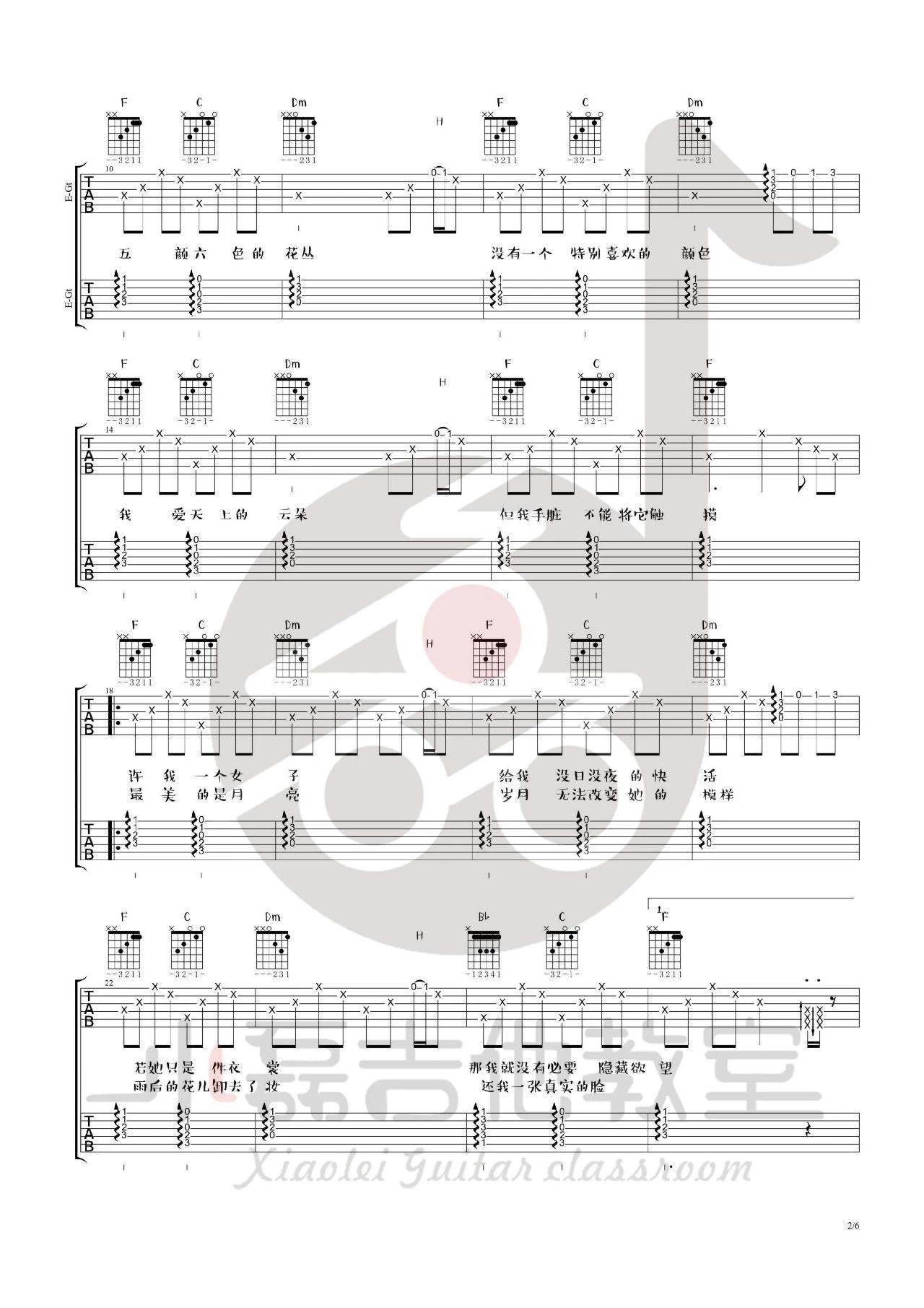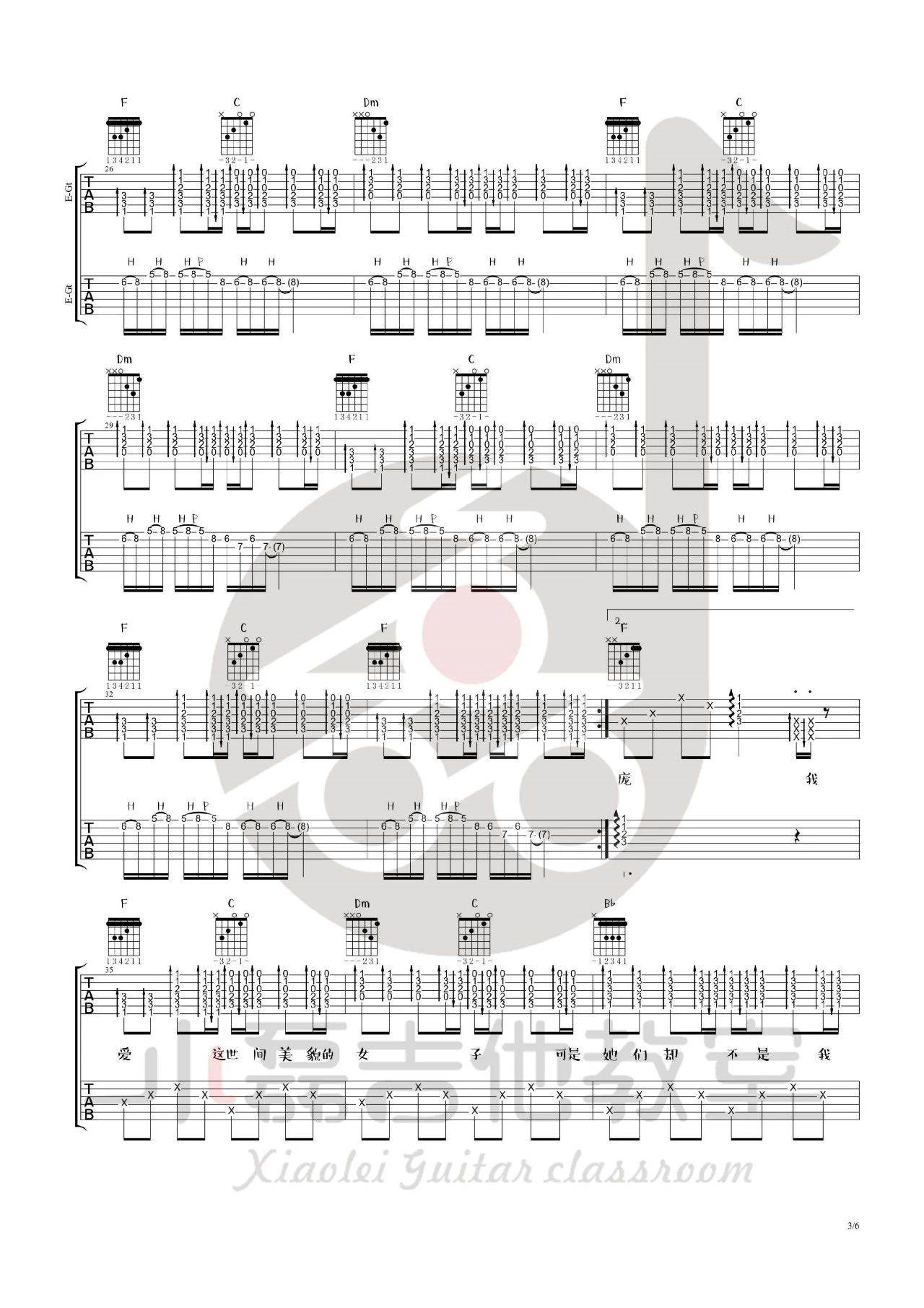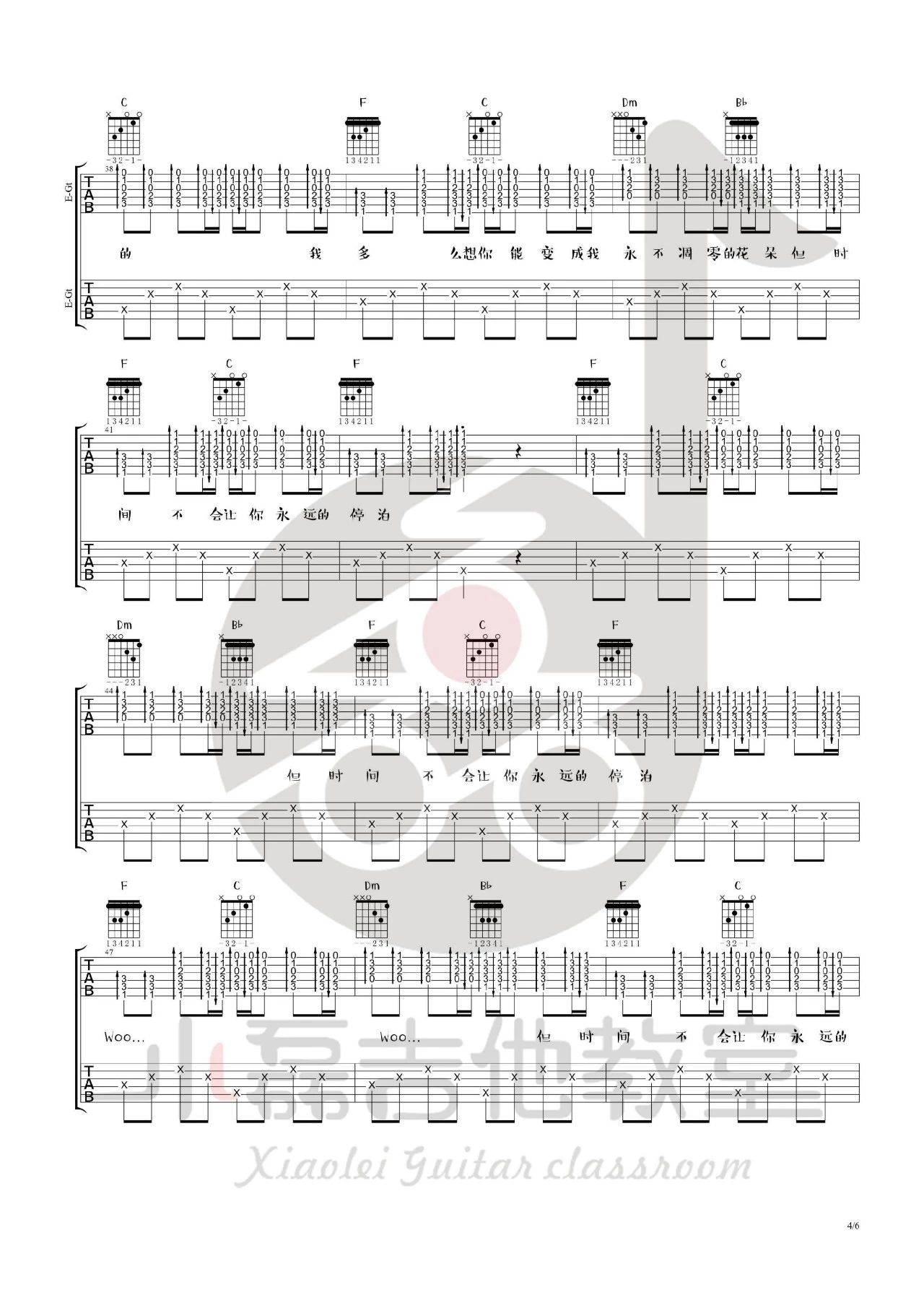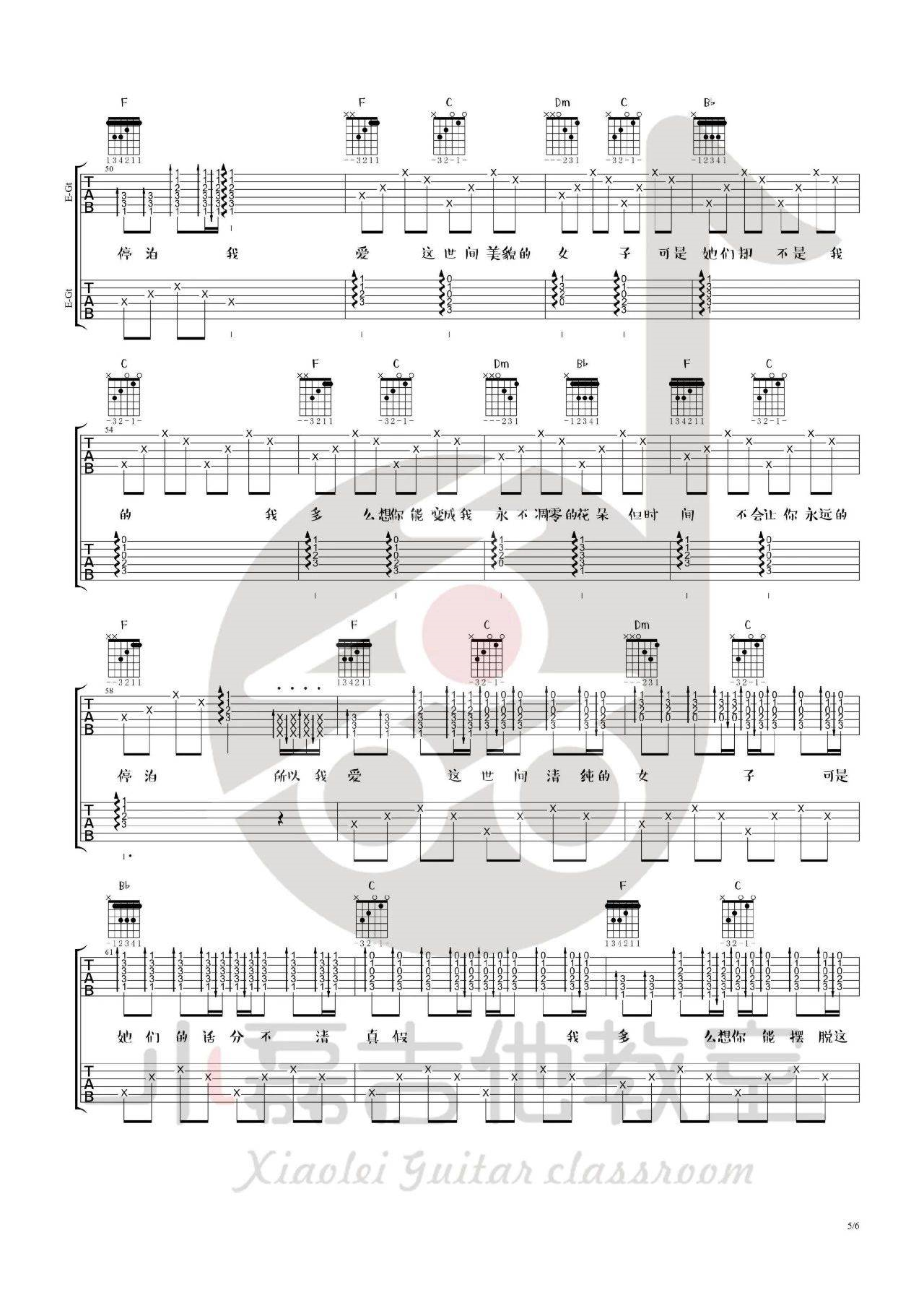《朵》以含蓄的意象编织出生命绽放与凋零的双重叙事,将植物生长周期隐喻为人类情感的盛衰历程。歌词中反复出现的"花瓣坠落"并非单纯的凋谢象征,而是暗含生命质感的转化过程——那些看似坠落的瞬间,实则是另一种形态的飞翔。具象的植物意象与抽象的情感体验形成镜像关系,晨露、根系、季风等自然元素构成情感嬗变的坐标系,在微观的植物细胞分裂中窥见宏观的人生际遇。文本通过植物器官的拟人化处理,巧妙消解了生命体与非生命体的界限,土壤中盘错的根系成为记忆网络的物质载体,光合作用被重新诠释为情感能量的转换装置。季节轮回的不可逆性与生命自我修复的可能性形成张力结构,在"腐烂滋养新生"的悖论中完成对创伤的美学救赎。歌词最终指向存在主义的终极命题:所有绽放都包含着凋谢的基因,而真正的永恒恰在于接受短暂性的勇气。这种以物观物的表达方式,使自然现象升华为哲学沉思的媒介,在草木枯荣间映照出人类命运的普遍图景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