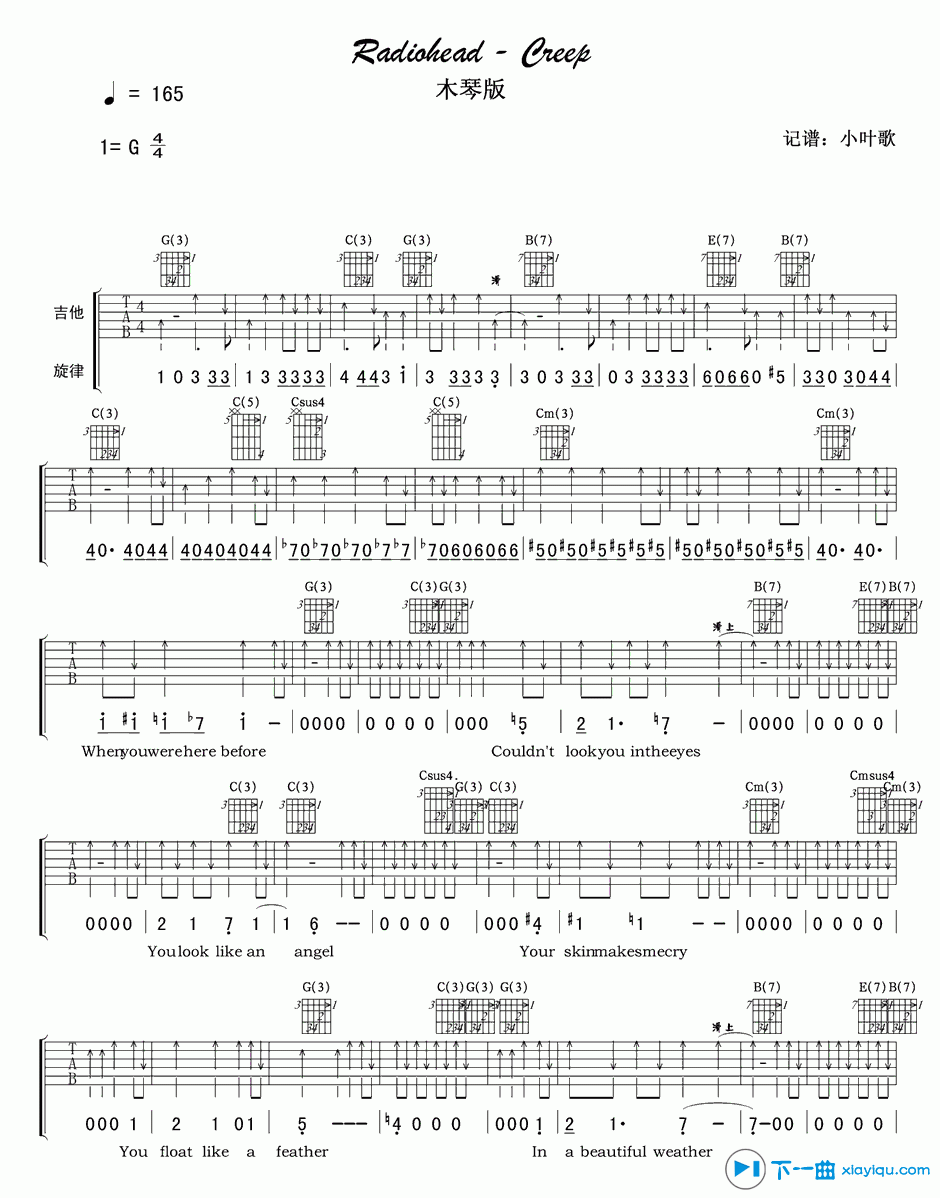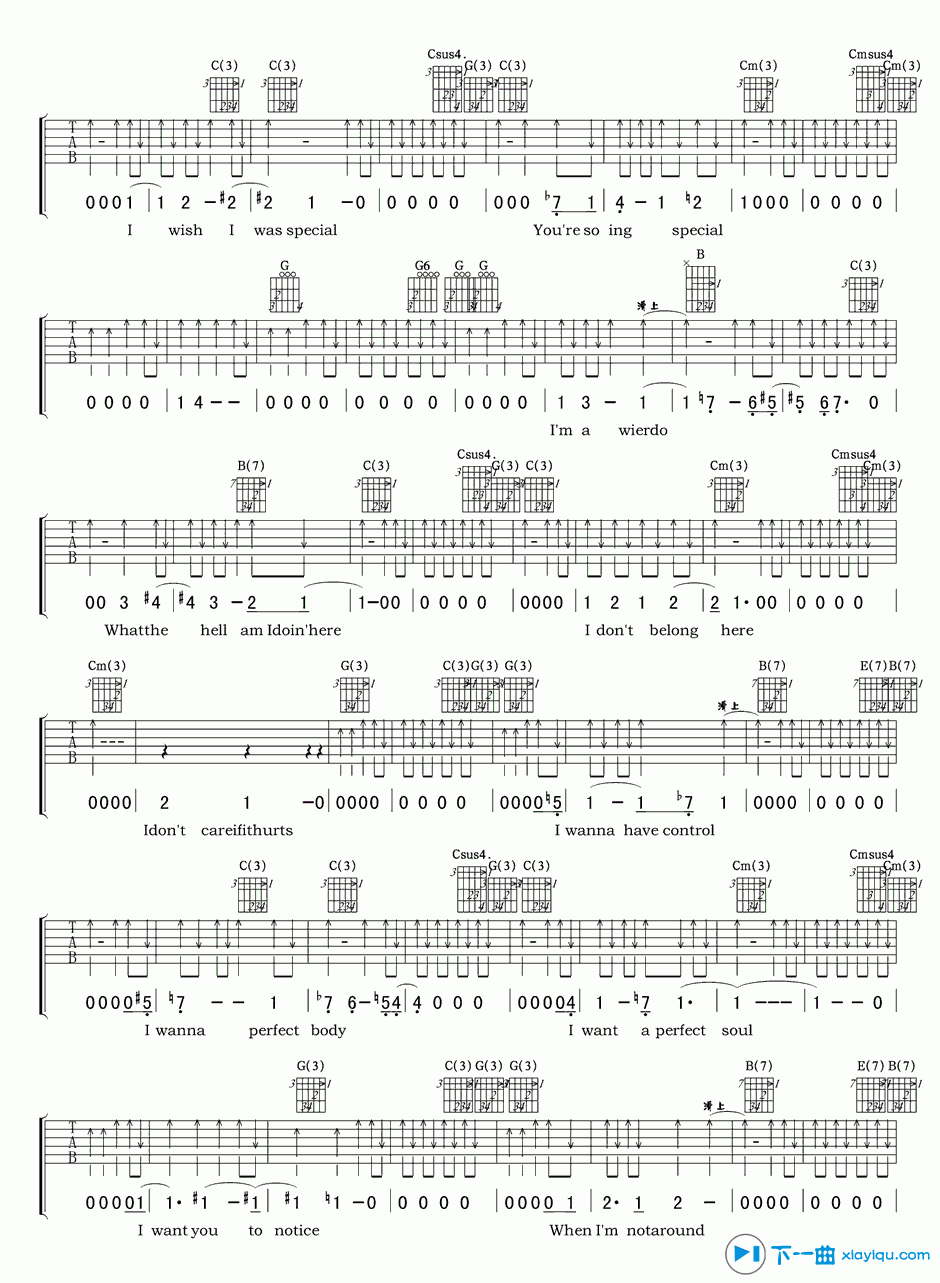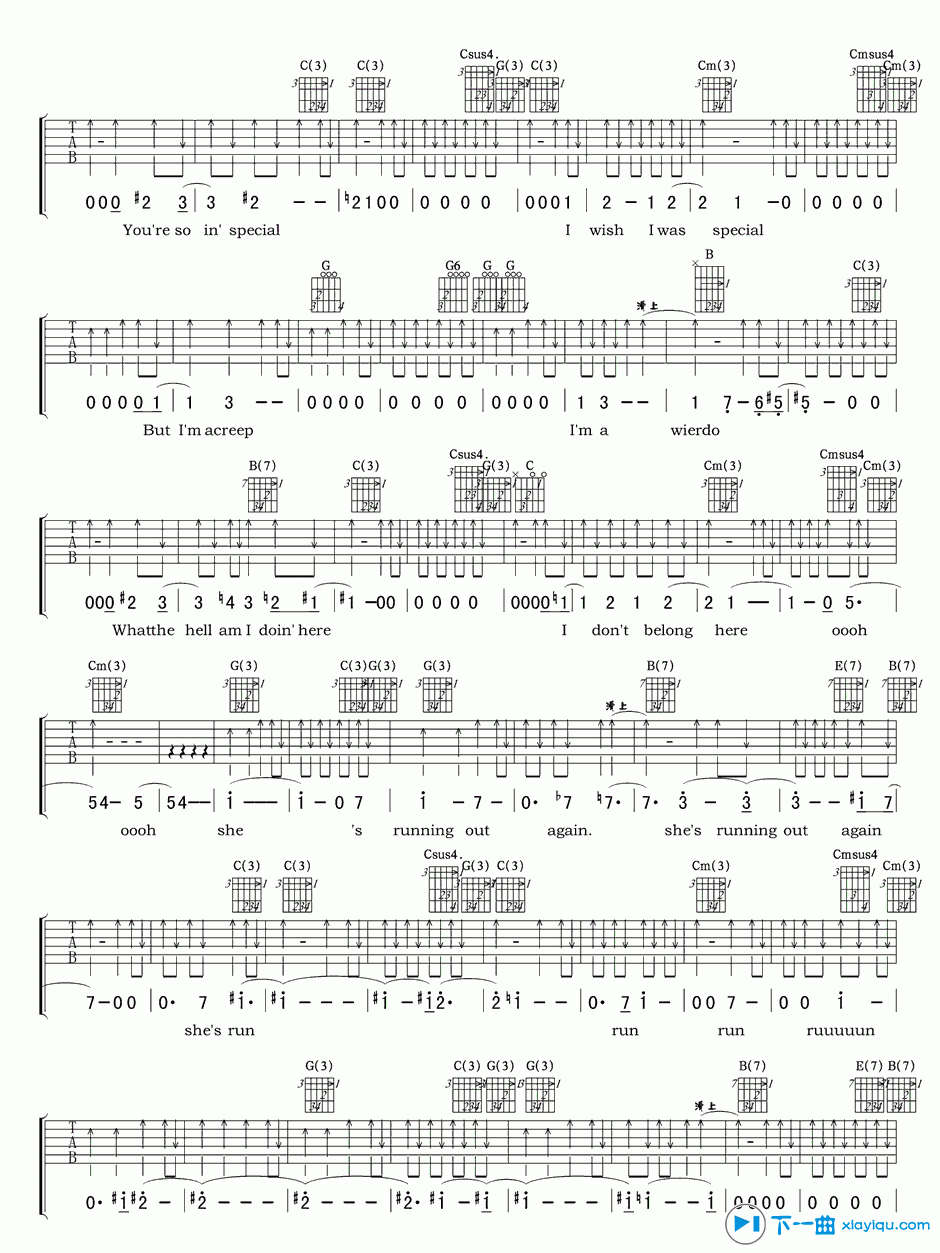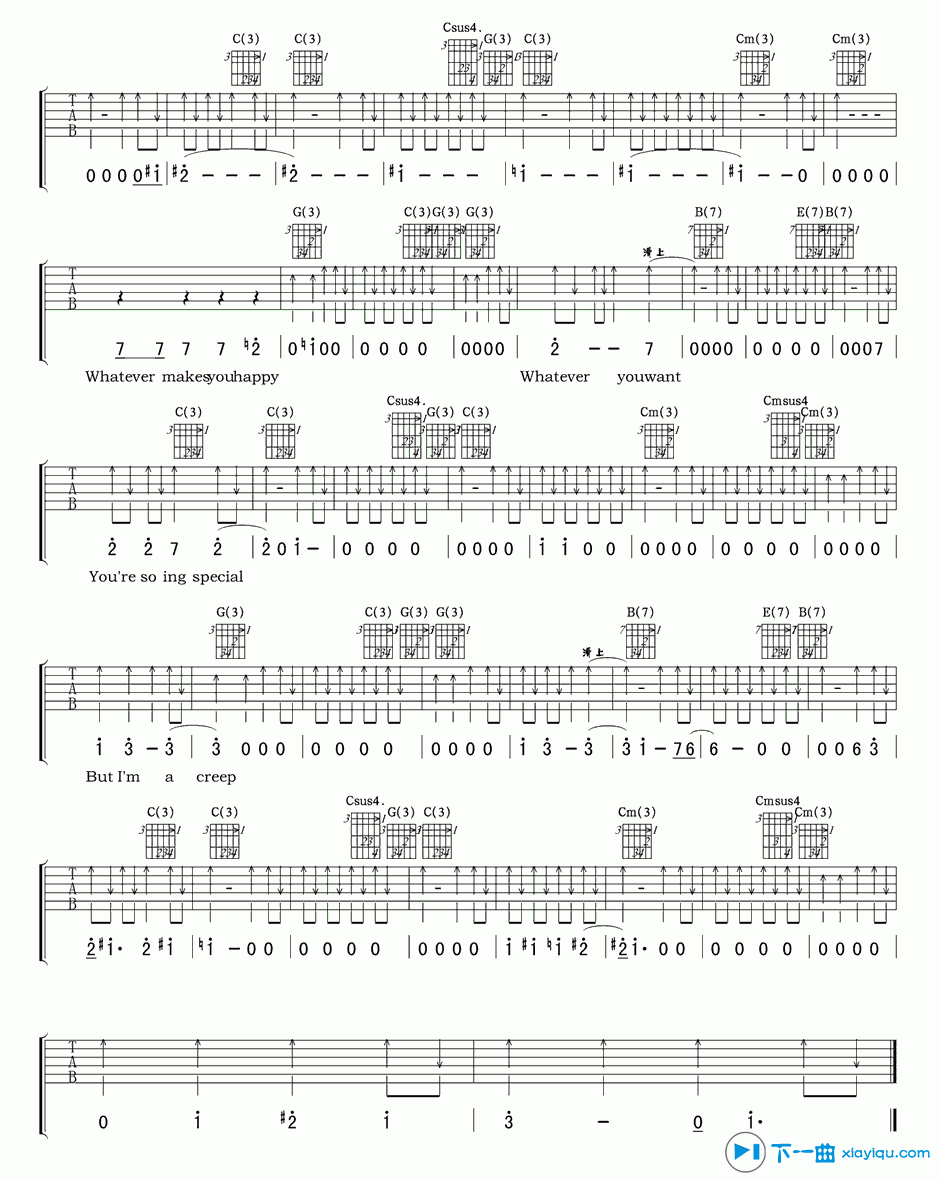《Creep》以极具冲击力的自白式表达,剖开了社会边缘人隐秘而灼痛的精神世界。歌词中反复出现的"怪胎"意象,既是他人投来的冰冷标签,也是自我认知中无法挣脱的枷锁,这种主客体错位的身份焦虑构成了整首歌的情感基底。当叙述者凝视那个"像天使般闪耀"的完美客体时,强烈的对比放大了其灵魂深处的撕裂感——既渴望被高贵灵魂救赎,又清醒认知自身与理想国度的永恒隔阂。音乐层面通过压抑的分解和弦与爆裂的失真音墙,具象化演绎了自卑与自负的激烈拉锯,那些突然拔高的嘶吼恰似灵魂在卑微处境的绝地反抗。"我想要完美躯体"的宣言,暴露出消费时代人类普遍的异化困境,当个体价值被物化为可量化的标准件,自我厌弃便成为时代精神的痼疾。而最终未能消解的疏离感,让这首歌超越简单的情爱叙事,成为所有格格不入者共同的精神图腾,在破碎的镜像中照见每个现代人内心深处那个瑟缩的"畸零人"。这种将伤口展览为勋章的勇气,恰恰构成了作品最打动人心的精神内核。